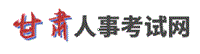近些年,“龙”这个字眼,常被译作“Loong”,这个现象在网络上比较普遍。
那个英文单词dragon以及其它语言里对应的词汇,原本意指欧洲神话中的虚构生物,体型巨大,性情凶猛,模样类似巨蜥,拥有硕大的蝙蝠式翅膀,能够飞翔,习惯捕食人类,并且喜爱喷射火焰进行攻击。这种生物的寓意相当负面,在东亚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看作是邪恶的标志。
杜拉更在欧洲神话里,常被当作邪恶象征使用,代表各种负面事物。外国媒体在报道时,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描绘成杜拉更,他的对手用这种比喻来攻击他。特朗普的支持者,则把政治正确等他们反对的东西,称作杜拉更,同时把特朗普塑造成斩除邪恶的古代英雄式人物。
这幅漫画的标题是杜拉更屠龙者,作者是保罗斯诺弗,创作于2015年8月26日。
所以,将“龙”翻译成“dragon”是极大的失误,对于海外人士而言,这仿佛是中国人在自诩为邪恶存在。
中国已经不再面临挨打和挨饿的困境,当前正努力克服挨骂的难题。然而将龙翻译成dragon,等于主动招致非议,为反华阵营丑化中国创造了机会,削弱了我国对外宣传的部分成效,阻碍了“一带一路”等涉外事务的顺利推进。所以应当尽快纠正将龙误译为dragon的做法。
我从2005年开始接触译龙课题,持续深入探究,累积了丰硕的文献资料更多公务员考试网题库就点击这里,并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次探讨交流。接下来,我将概述译龙课题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况,同时说明个人的研究进展。
1 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外国人开始翻译“龙”字
台岛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研究员李奭学的学生林虹秀所提交的文献证实,马可波罗在其东方见闻录里,已经将元朝宫殿内的龙饰称作dragon。
根据我找到的最早文献,是书籍Le Livre de Marco Polo(马可波罗的书)。这本书的书页上标明:是在1298年,由他本人讲述,由Rusticien用法语记录下来的,最终于1865年出版发行。书籍第268页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还有其他图画:龙,野兽,飞鸟,骑士等等。该书对pourtrais一词的解释为图绘,描绘。由此可见,这句话的含义是包含许多图像:比如龙,野兽,鸟,以及武士等等。
在引言部分CXXXIV页,dragon这个词还出现在对河流中文译名的说明里: Quelques jours après on franchit le fleuve Loung-ko(几天后,会渡过龙骨河),其中aux os de dragons是音译注解。
林虹秀觉得,咱们国家的龙跟西洋的龙,在模样特征上超过一半都差不多,因此西洋人把龙叫做dragon。我个人觉得,元朝军队既厉害又凶狠,或许是咱们国家的龙被称作dragon的另一个原因。
李奭学指出,现今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并非其手稿本,因而真伪问题难以判断。据他研究,马可波罗或许将元朝宫殿中的龙错认作蟒蛇,故而称之为drago。此外,他发现1322年来华的方济会士鄂图瑞克,在用拉丁文记录时,将元朝宫殿里的龙称作serpens。
笔者于鄂图瑞克1891年法文版《亚洲游记》第368页发现,同一段落中提及的动物是蛇类。然而在第329页里,作者在论及《山海经》这部典籍时,提及了dragon一词:全部这些创作都颇为引人入胜,它们摘自那部描绘山川海泽的著名著作《山海经》,其中不乏极富奇趣的篇章,在这些篇章中我们确实能见到些外形类人的怪物:比如Kou,它长着人的脸庞却拥有条龙的身体;......我们注意到有个怪物长着人脸,十分奇特,比如有个叫“鼓”的,它既有人的脸又有龙的身体;……)作者还为此配上了《山海经》中的图画。从这些来看,鄂图瑞克在形容蛇形躯体的龙时用了serpent这个词,而在形容马蹄形(或蜥蜴形)的龙时,则用了dragon这个词。
鄂图瑞克在其著作《亚洲游记》第194页至195页提及:中国流传一个故事,讲述鲟鱼每年农历三月会逆流而上进入黄河,若能闯过龙门口的险滩,这些鱼儿便会化身为龙。他所说的那个故事明显就是“鲤鱼跃过龙门”。这里的“鲟鱼”实际上是“鲤鱼”的别称,因为那个时期欧洲还没有鲤鱼。原文里的Loung是作者根据“龙”的发音写下来的。
1583年刊行的《葡汉辞典》将“龙”译作bicha-serpens,林虹秀将其意译为“类蛇巨物”;将“蛟”译为葡萄牙文drag?o,与拉丁文dracō或英文dragon读音相合。普遍认为这部词典出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罗明坚之手,不过学术界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并且该工具书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十分微薄。
龙华民,作为利玛窦的后续者,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大约在1602年将《圣若撒法始末》翻译成汉文时,把里面的dracō这个词,改成了“毒龙”或者“猛龙”这两个名称。李奭学提出看法,说“蛟”或者“龙”这两个字,通过欧洲人的翻译或者dracō被中文翻译,也许从此就在历史上确立了它们的用法。
1635年,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Semedo)以葡萄牙语创作了《大中国志》这部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借助利玛窦和罗明坚翻译“蛟”时使用的葡文drago,来转译《封禅书》里黄帝所骑的龙。换言之,曾德昭并未将“龙”与“蛟”加以区分。
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翻译中文版《圣经》,期间在澳门编撰了第一部《华英字典》作为辅助工具,当中“龙”字依照龙华民译法,先译为拉丁文dracō,再转译为英文dragon。马礼逊声望很高,因此后人多沿用这一译名。终于,中国龙和欧洲的杜拉更被混为一谈。
早在上一年,也就是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希曼便推出了《中国语法基础》这部著作,在该书中,他将“龙”这个字音标为loong。检索过程中还发现,一本1817年出版的英国外交官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里,记录了“the Loong-wang-Miao,或称龙王庙”,这明显是将“龙王庙”分别用音译和意译的方式呈现出来。自那时起,这个译名便沿用至今,比如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生产的龙凤香烟,其英文名写作“Loong Voong Cigarette”;海外华人的名字里“龙”字也采用此译法,武术界的李小龙,他的外文名之一是Lee Siu Loong。
根据前述考证可知,元代时期,“龙”或许已被称作dragon,并且至少与serpent并存使用,此后《葡汉辞典》的编撰者曾尝试区分“龙”与“蛟”,然而此举未能奏效,将“龙”译为dragon的译法因而得以沿袭至今。
个人认为,探究究竟是谁率先将龙与dragon进行翻译,并无太大价值。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极为纷繁,龙所承载的角色和象征内涵亦在持续演变之中。在封建社会时期,龙专属于皇室,用以彰显统治与权威;而在当今社会,普通民众则能够自由运用,借此抒发欢欣之情和美好期盼,代表中国及其文化。文字的根本功能在于精准而简洁地揭示事物当下的本质。如今龙的状况,若据此断定先辈翻译有误,那未免太过严苛;再者,即便先辈如此翻译,后人也不应墨守成规,这种想法同样有误。
这项研究的显著成果在于:证实了西方人在翻译“龙”时,除了采用dragon和serpent等意译方式外,早在十三世纪便已开始使用loung音译“龙”这个汉字,并且自十九世纪初起,他们又以loong为“龙”字标注发音,并以此进行“龙”的音译。由此可以明确,用loung或loong音译“龙”并非什么隐秘的、离经叛道的做法,更不是近年才被某些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译龙途径。实际上外国人音译他国特有事物名称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现象。
2 至少从十九世纪开始,有外国人认识到龙和杜拉更有显著差别
1882年,在美国邵武服务的华人牧师沃克撰写了一篇名为《宝塔,龙与风水》的论文,该文记录了他在当地的研究成果。他写道:龙通常被译为dragon, 它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就和鹰对我们的意义完全相同, 甚至更为重要。它是一种神秘而传奇的生物, 在诸多方面类似于西方神话中的dragon, 但却远胜于它。它不仅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 几乎被视作神圣的存在。它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体型庞大的生物,在诸多特征上与西方神话里的杜拉更颇为相似,却远远超越了杜拉更的境界。它不仅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还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禀赋。)
1923年,即民国十二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刊印了一本英文读物,该书篇幅不长,仅六十六页,书名是《The Chinese Dragon,龙》,内容阐明了中国龙与欧洲杜拉更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文献记载我们无从得知首位将英文“dragon”这一称谓与中国的“龙”概念相联系的人是谁,将伴随着该英文称谓的贬义标签强加给这一东方的海上主宰,显然有失公允,实属不妥,这种做法对它而言极不公平。中国的龙与通常被西方所接受的龙的概念,在三个显著方面存在差异,分别是外貌形态,性情脾气,以及人们赋予它的评价地位。……。中华神龙与西洋人所知的龙,存在三个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体态样貌,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大众对它们的认知观念。)
1931年2月12日,牛津大学汉语教授William Edward Soothill牧师在英国皇家亚洲文化协会发表演讲,他提到:“......在中国,龙向来带来好处,但西方的龙多数被视为坏东西,它们伤害百姓,劫走公主,还会激发像圣乔治那样的英雄去消灭它们。”)
早在1987年,国内有学者就提出龙与dragon不宜相互转换,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
1987年,翻译家吕炳洪教授发表文章提到:中国文化里,“龙”代表帝王,象征尊贵。民间有赛龙舟、挂龙灯的习俗。“龙凤呈祥”中,龙寓意好运。我国存在大量与龙相关的神话故事和说法,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比如有句俗语:“他在县里是条龙,到了省里成了条虫。”此处,“龙”比喻声势和权势。在英文语境里,龙(dragon)意味着凶狠(savagery,strife,terrible,maleficent)。当说“他的妻子是条龙”时,这个比喻带有非常无礼的贬损色彩。
1988年,阎云翔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发表文章指出:他始终认为,中国的龙既不同于西方的毒龙,也不同于印度的那伽,这三种神奇生物应当区分开来,不宜用一个名称来翻译,例如汉译佛经时将那伽译为龙,而一些英文著作又把龙译成dragon。
1991年,资深英语权威葛传槼强调:英文单词dragon形容人类时,意指令人畏惧之辈,而非令人敬仰之才,故而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实为祈愿子辈为祸,而非期盼子辈腾达。不论怎样,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时,诸如“人中龙”和“龙蟠凤逸”这类成语里的“龙”都不应该翻译成dragon。
1992年,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大津强调,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会运用各自的参照体系,解读特定词汇时总是依据这个体系,所以最终认知常常存在差异,。例如,所谓龙,于我们而言是崇高价值的代表,。然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它却常被视为不祥之兆,。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1993年,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范守义在文中指出:尽管存在对应词汇,但某些词语的指代范围及意义深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God与上帝(前者本意指天帝)、dragon与龙,或涉及哲学、文体学等领域的术语。这种情况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成为产生误解的关键原因。
2005年,译龙未能入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这一情况引发了社会大众对译龙问题的广泛关注。
2005年11月11日,北京奥运会评选吉祥物的结果公布,最广受关注的龙并未当选。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龙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不适合作为奥运会的象征。龙的形象在东方和西方有显著区别。西方人观念里的龙与我们珍视的情感象征并不一致,容易造成混淆。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活动,是展示华夏文明的绝佳平台,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标志。龙未能入选奥运会标志,让公众意识到龙的文化翻译并非微不足道的问题。
1月12日,中国太平洋学会与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形象?龙的正名”的学术艺术交流活动,该活动旨在澄清对龙的不同理解,组织方强调,西方语境中的“dragon”通常代表着邪恶,被视为凶恶与残暴的象征,它象征着那些具有压迫性的力量。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the Chinese dragon’,在西方文化作品的各个领域,‘中国龙’常与‘黄祸’和‘恶势力’牵连,屡遭误解和歪曲,活动建议以汉语拼音‘long’作为对中国龙的标准译名。
笔者注意到long在英文里使用频繁,含义丰富,不适合再作龙的对应名称,因而提议将龙改译为Loong。西安龙凤文化研究者庞进也曾在文章中主张用Loong翻译龙。后来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台湾学者蒙天祥在2004年就已发表文章,倡导将龙译为Loong。我国官方规范从二零一二年开始准许采用英文字母标示汉语声调标记,诸如“陕西”可转写为Shaanxi,借此与“山西”(Shanxi)加以区分。据此,将龙翻译成Loong的做法具备充分依据。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新闻晨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形象标志或许将更换”的文章,其副标题为“部分形象标志易引发歧义”,文中提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吴友富的看法:由于“龙”在英文语境中常被视为具有威严和侵略性的生物,因此主张对“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进行“再设计”。
吴教授的主张被看作是“舍弃龙”,因此激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对,紧接着,关于龙是否该被淘汰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得非常热烈。在这个阶段,重新诠释龙的观点被当作一种解决之道,讨论龙的问题第一次不再局限于学术圈,而是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8日,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专题《时空调查:是否为龙正洋命名?》,其中提及将龙音译为Loong的方案,并对此展开讨论,12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如何称呼你,中国龙》,同样报道了这一提议。十四日,美联社发布消息,接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中国日报进行了转载。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首场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举办,同时公布了《首场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其中说明:华夏龙与西洋dragon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形象非凡,主要寓意为正义和吉祥,后者外表狰狞,主要象征为邪恶和灾祸,建议将龙翻译为loong以示区分。
2015年3月全国两会于北京举行,政协委员岳崇呈递了《关于修正龙与dragon译法的建言》。2016年3月两会召开时,岳崇再度提交相关提议,倡议将龙译为Loong,人大代表王军亦表达了类似看法。2017年两会期间,岳崇第三次呈报相同内容提案。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和管理部门开始译龙为Loong。
“龙芯”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独立研制的通用中央处理器芯片,其英文原名初为Godson,后于2006年11月更名为Loongson。
2008年1月,腾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款网络游戏,这款游戏的中文名是龙,英文名称则为Loong。
浙江长龙航空企业诞生于二零一一年四月,其英文标识为Zhejiang Loong Airlines Co., Ltd.。由于外国人常将“长”字拼写为loong,所以loong字本身也蕴含着“长”字之意,因而“长龙航空”翻译为Loong Air便构成了一种别致的对仗。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翼龙”多用途侦察攻击无人机,于2011年6月亮相巴黎航展,其英文名称是Wing Loong,这个名称的中文意译为翼龙。
二零一七年五月,一部名为《龙之战》的影片海报问世,该影片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多家机构共同制作完成,其外文译名为The War of Loong。
一些个体也采用这种方式翻译龙,比如用Loong作为个人网络代号,或是把它与其他字符或词句搭配后登记网址。
目前包含Loong词条的在线英汉词汇表有爱词霸,海词词典,n词酷,百度百科,里氏词典,网址是www.dict.li。另有一个专门的Loong词条的英英词汇表,即Urban Dictionary。维基百科收录了龙,并链接到中国龙词条,自由词典也使用了相同的方式。
龙开始用音译称呼时,一些承载中国文化的词语也被音译了,2009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正式通知,为了让这项运动在全球更广泛地传播,决定把“中国象棋”的名称改成“象棋”,它的英文叫法还是用“Xiangqi”。
这件事影响深远,不过作者有个小想法:为了防止产生“英语特殊化”的情况,我国官方恰当的说法应当是:“Xiangqi是‘象棋’的罗马字母转写”,而无需特别指出它是“英文译名”。当Xiangqi被引入不同国家语言时,为了方便该国语言使用者,也理应根据各国语言的拼写规则,进行相应的修改。X和Q在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Xiangqi的英文读音并非“象棋”,所以,合适的英文译名应为Shiangchi,这种拼写方式更贴近“象棋”在汉语中的发音。韩国首都是首尔,其外文名称在不同语言中也有差异。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主张京剧的英文名称应为Jingju,不宜称为Peking Opera。几年之后,戏曲界就此达成一致并着手实践。如今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均采用Jingju作为对外称谓。
杜拉更(dragon)在外国的时政图画里,代表着几乎所有糟糕的事物
多年间,笔者竭尽所能,借助网络等渠道,搜集了数百张描绘杜拉更的外国政治漫画,时间跨度达数百年之久。在这些画作里,杜拉更所代表的事物几乎全带有贬义色彩,正面形象不足百分之一。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的讽刺画家常把对方军队描绘成怪物,把己方领导人比如拿破仑和英国君主则塑造为斩杀怪物的勇士,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队及其指挥官常被讽刺成怪物,而林肯总统一众北方将领则被形容为重创怪物的英雄。
十九世纪末期,于俄国与东瀛的冲突期间,东瀛人士被俄方画师刻画为凶戾的杜拉更形象,而俄方则被塑造为遭受东瀛杜拉更残暴侵袭的仁人志士、无畏面对杜拉更的圣洁女性。紧接着在巴尔干地区的战事中,奥斯曼王朝被呈现为行将就木的杜拉更模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的形象都被刻画得极其凶残,如同怪物一般。俄罗斯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红军的艺术家以及白军的画师,都将对手描绘成这种邪恶的化身,而己方的士兵则被画成在奋勇地攻击这些怪物。
二战期间,一些反抗法西斯的艺术家将纳粹德国描绘成恶龙,而纳粹德国的画师们则把抵抗法西斯的国家描绘成恶龙。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庆祝二战胜利时,依然将纳粹德国称作恶龙。事实上,俄罗斯国徽中心就刻有英雄斩杀恶龙的形象。
图二描绘波兰对抗纳粹暴政的场景,名为波兰勇斗纳粹恶魔,系Arthur Szyk所作,完成于1939年。
在反恐斗争中,西洋漫画师常把恐怖组织刻画成恶魔,而阿拉伯和伊朗的绘图者则把美国和以色列等描绘成恶魔。
国内外政治博弈里,敌对势力同样称作杜拉更,国内局部争端中也是如此,经济困境、负债、财政失衡、天灾人祸、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病症、瘟疫、火灾、核污染、二手烟、欺骗手段、坏脾气、粗鲁言辞、数学难题等等,众多负面事物都被漫画家描绘成杜拉更。
6 中国外译部门的专家学者坚持反对重新译龙
中国外语界普遍清楚dragon这个词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也明白建议将龙翻译成Loong以及实际应用的情形,不过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倾向于继续将龙译为dragon。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这项工程由教育部、国家语委负责牵头,还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到了2017年,这个工程发布了四百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解释和英文翻译,不过“龙”这个术语还是被翻译成了dragon。
章思英作为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西方对于“龙”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译审专家之所以继续将“龙”译为dragon,是由于译审团队包含外交部、外文局、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专家,这些专家普遍认为,在过往中外交往较少的时期,外国人对中国人为何崇拜一个看似凶狠的图腾形象可能会感到困惑。如今,海外许多读者已能区分中国龙与西方龙,随着中西互动日益密切,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里,也时常出现龙的正面形象了。
这些专家的思维实在难以理解,既然明白“‘龙’的寓意在东西方差异极大”,为何还要让它们共享一个称谓?就连南方的橘到了北方出现变化,尚且要改称为“枳”。龙与杜拉更是迥异,并且是中华文化的标志,其译名问题至关重要,却反而没能获得一个专属的叫法?外国日常饮食也各有其称谓:比如披萨、汉堡、寿司、巧克力、可乐,可对于十几亿中国人自称源自的龙,为何却如此吝啬命名呢?
文艺作品的制作者为了招徕读者和观众,会反其道而行之,独树一帜,把常被看作是有害的动物描绘成正面形象。这种情况很常见,但并不能消除这些动物固有的不良寓意。尽管米老鼠十分聪明讨喜,但可以断定,相当多的中国家庭在给孩子取名字时不会选用“鼠”这个字。
译龙项目虽然有过理解偏差,但该工程仍取得显著成果,它将众多中国独有文化概念采用音译方式处理,比如“君子”对应Junzi,“风骨”对应Fenggu,“仁”对应Ren(不过个人认为这个译法过于简略,换成Renship更佳)。
7 “不译”不等于“不释”,“零翻译”不是“零注释”
许多人忧虑外国友人无法理解音译的中国特色词汇,缘于未意识到,音译仅是初始环节,其后需为新生造的音译词汇配备外文说明,说明中可运用图像、声响及影像资料,或促使外国人经由接触实体来领会其意涵。
外来事物传入国内时,很多都采用了音译的方式,这些名称在国内却非常普及,即便是三岁孩童也能明白“汉堡”和“可乐”的意思,我们何必担忧外国成年人无法理解“龙”和“京剧”的称谓呢?
外来语每日都在增添新词汇和新缩写,外国人通常在它们初次见于文章或谈话时稍作说明。笔者将dragon一词译为“杜拉更”,在该篇首次出现时,附加了标注“(dragon)”,读者应当明白。
外国人在翻译中国特有名词时,往往比国人更热衷采用音译方式,比如Kongfu被称为功夫,Fengshui被称为风水,Jiaozi被称为饺子,Dama被称为大妈,Tuhao被称为土豪,Chengguan被称为城管,Wanghong被称为网红,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当音译比意译更为精练时,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采用音译方法。中国人现已不再使用“意大利馅饼”这一说法,转而选用音译词“披萨”。外国友人同样倾向于简便处理。一旦他们了解到“武术”存在一个更为简洁的对应词“Kongfu”,便立刻改用这个词语了2006年,有外国友人致信探讨翻译龙之事,他们全都采用Loong一词,而非冗长的Chinese Dragon,即便是那位持反对意见改译龙观点的美国学者亦是如此。
持之以恒同样关键。1948年,粤菜师傅在海外将“点心”称作Dim Sum,持续沿用至今。如今,洋人反觉得把中国简餐称作Snack不妥,主张该用Dim Sum。此名称还早被权威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韦氏辞典)收录。
本国文化特色词汇在异国文化里缺乏相匹配的术语,为了精准传递本国文化内涵,创造专属的外文表达形式十分关键。从理论层面、技术手段以及法规制度来看,这些方面均不存在障碍,主要难点在于思想层面,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专家需要打破固有思维,更新认知观念,有效推进此项任务。